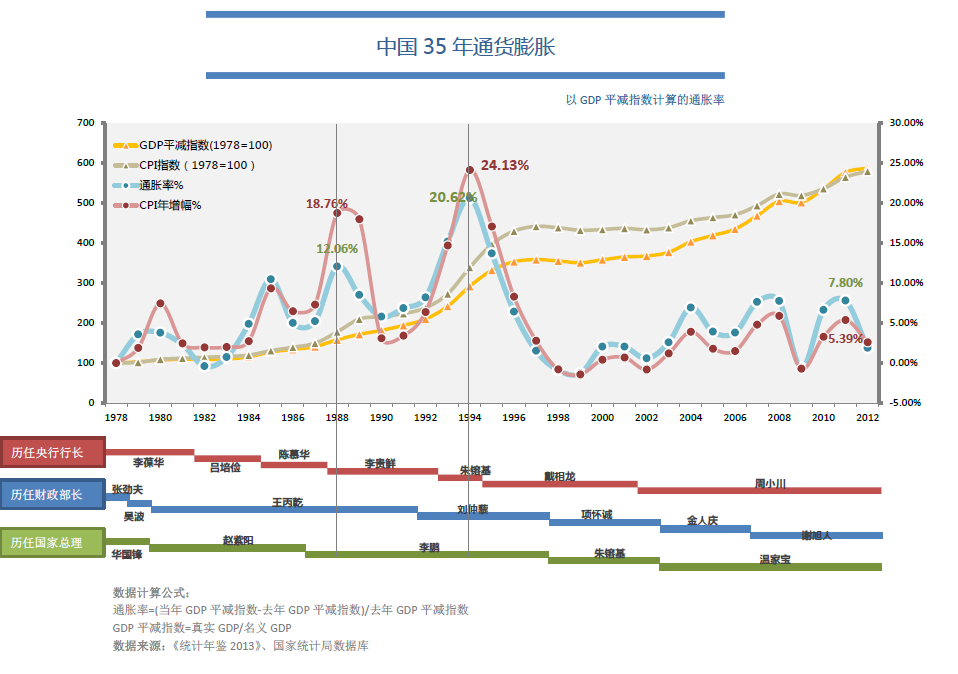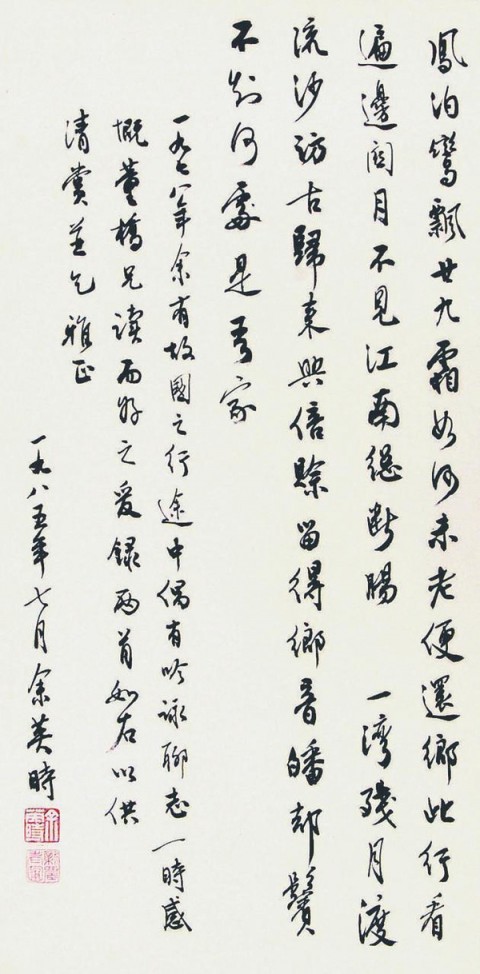[转]深入理解HTTP消息头
什麼是HTTP Headers
HTTP是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的缩寫,整個WWW都在使用這種協定,幾乎你在流覽器裏看到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通過HTTP協定來傳輸的,比如這篇文章。
HTTP Headers是HTTP請求和相應的核心,它承載了關於用戶端流覽器,請求頁面,伺服器等相關的資訊。

示例
當你在流覽器位址欄裏鍵入一個URL,你的流覽器會將類似如下的HTTP請求:
GET /tutorials/other/top-20-mysql-best-practices/ HTTP/1.1 (Request line) Host: net.tutsplus.com User-Agent: Mozilla/5.0 (Windows; U; Windows NT 6.1; en-US; rv:1.9.1.5) Gecko/20091102 Firefox/3.5.5 (.NET CLR 3.5.30729) Accept: text/html,application/xhtml+xml,application/xml;q=0.9,* / <em>;q=0.8 Accept-Language: en-us,en;q=0.5 Accept-Encoding: gzip,deflate Accept-Charset: ISO-8859-1,utf-8;q=0.7,</em>;q=0.7 Keep-Alive: 300 Connection: keep-alive Cookie: PHPSESSID=r2t5uvjq435r4q7ib3vtdjq120 Pragma: no-cache Cache-Control: no-cache
第一行被稱為Request Line 它描述的是這個請求的基本資訊,剩下的就是HTTP Headers了。
請求完成之後,你的流覽器可能會收到如下的HTTP回應:
HTTP/1.x 200 OK (state line) Transfer-Encoding: chunked Date: Sat, 28 Nov 2009 04:36:25 GMT Server: LiteSpeed Connection: close X-Powered-By: W3 Total Cache/0.8 Pragma: public Expires: Sat, 28 Nov 2009 05:36:25 GMT Etag: "pub1259380237;gz" Cache-Control: max-age=3600, public Content-Type: text/html; charset=UTF-8 Last-Modified: Sat, 28 Nov 2009 03:50:37 GMT X-Pingback: http://net.tutsplus.com/xmlrpc.php Content-Encoding: gzip Vary: Accept-Encoding, Cookie, User-Agent
第一行被稱為Status Line,它之後就是HTTP Headers,空行完了就開始輸出內容了(在這個案例中是一些HTML輸出)。
但你查看頁面源代碼卻不能看到HTTP Headers,雖然它們連同你能看到的東西一起被傳送至流覽器。
這個HTTP請求也發出了一些其他資源的接收請求,例如圖片,CSS檔,JS文件等等。
下面我們來看看細節。
怎樣才能看到HTTP Headers
下面這些FireFox擴展能夠幫助你分析HTTP Headers:
- Firebug
-
在PHP中:
getallheaders()用來獲取請求Header. 你也可以使用$_SERVER陣列.headers_list()用來獲取回應Header.
文章下面將會看到一些使用PHP示範的例子。
HTTP Request 的結構

被稱作first line的第一行包含三個部分:
method表明這是何種類型的請求. 最常見的請求類型有GET,POST和HEAD.path體現的是主機之後的路徑. 例如,當你請求http://net.tutsplus.com/tutorials/other/top-20-mysql-best-practices/時 , path 就會是/tutorials/other/top-20-mysql-best-practices/.protocol包含有HTTP和版本號, 目前流覽器都會使用1.1.
剩下的部分每行都是一個Name:Value對。它們包含了各式各樣關於請求和你流覽器的資訊。
例如User-Agent就表明了你流覽器版本和你所用的作業系統。
Accept-Encoding會告訴伺服器你的流覽可以接受類似gzip的壓縮輸出。
這些headers大部分都是可選的。
HTTP 請求甚至可以被精簡成這樣子:
GET /tutorials/other/top-20-mysql-best-practices/ HTTP/1.1 Host: net.tutsplus.com
並且你仍舊可以從伺服器收到有效的回應。
請求類型
三種最常見的請求類型是:GET,POST 和 HEAD ,從HTML的編寫過程中你可能已經熟悉了前兩種。
GET:獲取一個文檔
大部分被傳輸到流覽器的HTML,images,JS,CSS, … 都是通過GET方法發出請求的。它是獲取資料的主要方法。
例如,要獲取Nettuts+ 的文章,http request 的第一行通常看起來是這樣的:
GET /tutorials/other/top-20-mysql-best-practices/ HTTP/1.1
一旦HTML載入完成,流覽器將會發送 GET 請求去獲取圖片,就像下面這樣:
GET /wp-content/themes/tuts_theme/images/header_bg_tall.png HTTP/1.1
表單也可以通過 GET 方法發送,下面是個例子:
First Name: Last Name:
當這個表單被提交時,HTTP request 就會像這樣:
GET /foo.php?first_name=John&last_name=Doe&action=Submit HTTP/1.1
…
你可以將表單輸入通過附加進查詢字串的方式發送至伺服器。
POST :發送資料至伺服器
儘管你可以通過 GET 方法將資料附加到URL中傳送給伺服器,但在很多情況下使用 POST 發送資料給伺服器更加合適。通過 GET 發送大量資料是不現實的,它有一定的局限性。
用 POST 請求來發送表單數據是普遍的做法。我們來吧上面的例子改造成使用 POST 方式:
First Name: Last Name:
提交這個表單會創建一個如下的HTTP請求:
POST /foo.php HTTP/1.1 Host: localhost User-Agent: Mozilla/5.0 (Windows; U; Windows NT 6.1; en-US; rv:1.9.1.5) Gecko/20091102 Firefox/3.5.5 (.NET CLR 3.5.30729) Accept: text/html,application/xhtml+xml,application/xml;q=0.9,* / <em>;q=0.8 Accept-Language: en-us,en;q=0.5 Accept-Encoding: gzip,deflate Accept-Charset: ISO-8859-1,utf-8;q=0.7,</em>;q=0.7 Keep-Alive: 300 Connection: keep-alive Referer: http://localhost/test.php Content-Type: application/x-www-form-urlencoded Content-Length: 43 first_name=John&amp;last_name=Doe&amp;action=Submit
這裏有三個需要注意的地方:
- 第一行的路徑已經變為簡單的
/foo.php, 已經沒了查詢字串。 - 新增了
Content-Type和Content-Lenght Header,它提供了發送資訊的相關資訊. - 所有資料都在headers之後,以查詢字串的形式被發送.
POST方式的請求也可用在AJAX,應用程式,cURL … 之上。並且所有的檔上傳表單都被要求使用 POST 方式。
HEAD:接收Header資訊
HEAD 和GET很相似,只不過 HEAD 不接受HTTP回應的內容部分。當你發送了一個 HEAD 請求,那就意味著你只對HTTPHeader感興趣,而不是文檔本身。
這個方法可以讓流覽器判斷頁面是否被修改過,從而控制緩存。也可判斷所請求的文檔是否存在。
例如,假如你的網站上有很多鏈結,那麼你就可以簡單的給他們分別發送 HEAD 請求來判斷是否存在死鏈,這比使用GET要快很多。
HTTP回應結構
當流覽器發送了HTTP請求之後,伺服器就會通過一個 HTTP response 來回應這個請求。如果不關心內容,那麼這個請求看起來會是這樣的:

第一個有價值的資訊就是協定。目前伺服器都會使用 HTTP/1.x 或者 HTTP/1.1 。
接下來一個簡短的資訊代表狀態。代碼200意味著我們的請求已經發送成功了,伺服器將會返回給我們所請求的文檔,在Header資訊之後。
我們都見過404頁面。當我向伺服器請求一個不存在的路徑時,伺服器就用用404來代替200回應我們。
餘下的回應內容和HTTP請求相似。這些內容是關於伺服器軟體的,頁面/檔何時被修改過,mime type 等等…
同樣,這些Header資訊也是可選的。
HTTP狀態碼
200用來表示請求成功.300來表示重定向.400用來表示請求出現問題.500用來表示伺服器出現問題.
200 成功 (OK)
前文已經提到,200 是用來表示請求成功的。
206 部分內容 (Partial Content)
如果一個應用只請求某範圍之內的檔,那麼就會返回206.
這通常被用來進行下載管理,中斷點續傳或者檔分塊下載。
404 沒有找到 (Not Found)

很容易理解
401 未經授權 (Unauthorized)
受密碼保護的頁面會返回這個狀態。如果你沒有輸入正確的密碼,那麼你就會在流覽器中看到如下的資訊:

注意這只是受密碼保護頁面,請求輸入密碼的彈出框是下面這個樣子的:

403 被禁止(Forbidden)
如果你沒有許可權訪問某個頁面,那麼就會返回403狀態。這種情況通常會發生在你試圖打開一個沒有index頁面的檔夾。如果伺服器設置不允許查看目錄內容,那麼你就會看到403錯誤。
其他一些方式也會發送許可權限制,例如你可以通過IP位址進行阻止,這需要一些htaccess的協助。
order allow,deny deny from 192.168.44.201 deny from 224.39.163.12 deny from 172.16.7.92 allow from all
302(或307)臨時移動(Moved Temporarily) 和 301 永久移動(Moved Permanently)
這兩個狀態會出現在流覽器重定向時。例如,你使用了類似 bit.ly 的網址縮短服務。這也是它們如何獲知誰點擊了他們鏈結的方法。
302和301對於流覽器來說是非常相似的,但對於搜索引擎爬蟲就有一些差別。打個比方,如果你的網站正在維護,那麼你就會將用戶端流覽器用302重定向到另外一個位址。搜索引擎爬蟲就會在將來重新索引你的頁面。但是如果你使用了301重定向,這就等於你告訴了搜索引擎爬蟲:你的網站已經永久的移動到了新的位址。
500 伺服器錯誤(Internal Server Error)

這個代碼通常會在頁面腳本崩潰時出現。大部分CGI腳本都不會像PHP那樣輸出錯誤資訊給流覽器。如果出現了致命的錯誤,它們只會發送一個500的狀態碼。這時需要查看伺服器錯誤日誌來排錯。
完整的列表
你可以在這裏找到完整的HTTP 狀態碼說明。
HTTP Headers 中的 HTTP請求
現在我們來看一些在HTTP headers中常見的HTTP請求資訊。
所有這些Header資訊都可以在PHP的 $_SERVER 陣列中找到。你也可以用getallheaders() 函數一次性獲取所有的Header資訊。
Host
一個HTTP請求會發送至一個特定的IP位址,但是大部分伺服器都有在同一IP位址下託管多個網站的能力,那麼伺服器必須知道流覽器請求的是哪個功能變數名稱下的資源。
Host: rlog.cn
這只是基本的主機名,包含功能變數名稱和子級功能變數名稱。
在PHP中,可以通過 $_SERVER['HTTP_HOST'] 或 $_SERVER['SERVER_NAME'] 來查看。
User-Agent
User-Agent: Mozilla/5.0 (Windows; U; Windows NT 6.1; en-US; rv:1.9.1.5) Gecko/20091102 Firefox/3.5.5 (.NET CLR 3.5.30729)
這個Header可以攜帶如下幾條資訊:
- 流覽器名和版本號.
- 作業系統名和版本號.
- 默認語言.
這就是某些網站用來收集訪客資訊的一般手段。例如,你可以判斷訪客是否在使用手機訪問你的網站,然後決定是否將他們引導至一個在低解析度下表現良好的移動網站。
在PHP中,可以通過 $_SERVER['HTTP_USER_AGENT'] 來獲取User-Agent
if ( strstr($_SERVER['HTTP_USER_AGENT'],'MSIE 6') ) {
echo "Please stop using IE6!";
}
Accept-Language
Accept-Language: en-us,en;q=0.5
這個資訊可以說明用戶的默認語言設置。如果網站有不同的語言版本,那麼就可以通過這個資訊來重定向用戶的流覽器。
它可以通過逗號分割來攜帶多國語言。第一個會是首選的語言,其他語言會攜帶一個 q 值,來表示用戶對該語言的喜好程度 (0~1) 。
在PHP中用 $_SERVER["HTTP_ACCEPT_LANGUAGE"] 來獲取這一資訊。
if (substr($_SERVER['HTTP_ACCEPT_LANGUAGE'], 0, 2) == 'fr') {
header('Location: http://french.mydomain.com');
}
Accept-Encoding
Accept-Encoding: gzip,deflate
大部分的流覽器都支援gzip壓縮,並會把這一資訊報告給伺服器。這時伺服器就會壓縮HTML發送給流覽器。這可以減少近80%的檔案大小,以節省下載時間和頻寬。
在PHP中可以使用 $_SERVER["HTTP_ACCEPT_ENCODING"] 獲取該資訊。
然後調用 ob_gzhandler() 方法時會自動檢測該值,所以你無需手動檢測。
// enables output buffering
// and all output is compressed if the browser supports it
ob_start('ob_gzhandler');
If-Modified-Since
如果一個頁面已經在你的流覽器中被cache,那麼你下次流覽時流覽器將會檢測文檔是否被修改過,那麼它就會發送這樣的Header:
If-Modified-Since: Sat, 28 Nov 2009 06:38:19 GMT
如果自從這個時間以來未被修改過,那麼伺服器將會返回 304 Not Modified ,而且不會再返回內容。流覽器將自動去緩存中讀取內容
在PHP中,可以用 $_SERVER['HTTP_IF_MODIFIED_SINCE'] 來檢測。
// assume $last_modify_time was the last the output was updated
// did the browser send If-Modified-Since header?
if(isset($_SERVER['HTTP_IF_MODIFIED_SINCE'])) {
// if the browser cache matches the modify time
if ($last_modify_time == strtotime($_SERVER['HTTP_IF_MODIFIED_SINCE'])) {
// send a 304 header, and no content
header("HTTP/1.1 304 Not Modified");
exit;
}
}
還有一個叫 Etag 的HTTP頭資訊,它被用來確定緩存的資訊是否正確,稍後我們將會解釋它。
Cookie
顧名思義,他會送出流覽器中存儲的Cookie資訊給伺服器。
Cookie: PHPSESSID=r2t5uvjq435r4q7ib3vtdjq120; foo=bar
它是用分號分割的一組名值對。Cookie也可以包含session id。
在PHP中,單一的Cookie可以訪問 $_COOKIE 陣列獲得。你可以直接用 $_SESSION array 獲取session變數。如果你需要session id,那麼你可以使用 session_id() 函數代替cookie。
echo $_COOKIE['foo']; // output: bar echo $_COOKIE['PHPSESSID']; // output: r2t5uvjq435r4q7ib3vtdjq120 session_start(); echo session_id(); // output: r2t5uvjq435r4q7ib3vtdjq120
Referer
顧名思義, Header將會包含referring url信息。
例如,我訪問Nettuts+的主頁並點擊了一個鏈結,這個Header資訊將會發送到流覽器:
Referer: http://net.tutsplus.com/
在PHP中,可以通過 $_SERVER['HTTP_REFERER'] 獲取該值。
if (isset($_SERVER['HTTP_REFERER'])) {
$url_info = parse_url($_SERVER['HTTP_REFERER']);
// is the surfer coming from Google?
if ($url_info['host'] == 'www.google.com') {
parse_str($url_info['query'], $vars);
echo "You searched on Google for this keyword: ". $vars['q'];
}
}
// if the referring url was:
// http://www.google.com/search?source=ig&hl=en&rlz=&=&q=http+headers&aq=f&oq=&aqi=g-p1g9
// the output will be:
// You searched on Google for this keyword: http headers
You may have noticed the word “referrer” is misspelled as “referer”. Unfortunately it made into the official HTTP specifications like that and got stuck.
Authorization
當一個頁面需要授權,流覽器就會彈出一個登入視窗,輸入正確的帳號後,流覽器會發送一個HTTP請求,但此時會包含這樣一個Header:
Authorization: Basic bXl1c2VyOm15cGFzcw==
包含在Header的這部分資訊是base64 encoded。例如,base64_decode('bXl1c2VyOm15cGFzcw==') 會被轉化為 myuser:mypass 。
在PHP中,這個值可以用 $_SERVER['PHP_AUTH_USER'] 和 $_SERVER[‘PHP_AUTH_PW’]` 獲得。
更多細節我們會在WWW-Authenticate部分講解。
HTTP Headers 中的 HTTP回應
現在讓我瞭解一些常見的HTTP Headers中的HTTP回應資訊。
在PHP中,你可以通過 header() 來設置Header回應資訊。PHP已經自動發送了一些必要的Header資訊,如 載入的內容,設置 cookies 等等… 你可以通過 headers_list() 函數看到已發送和將要發送的Header資訊。你也可以使用 headers_sent() 函數來檢查Header資訊是否已經被發送。
Cache-Control
w3.org 的定義是:”The Cache-Control general-header field is used to specify directives which MUST be obeyed by all caching mechanisms along the request/response chain.” 其中”caching mechanisms” 包含一些你ISP可能會用到的 閘道和代理資訊。
例如:
Cache-Control: max-age=3600, public
public 意味著這個回應可以被任何人cache,max-age 則表明了該cache有效的秒數。允許你的網站被cache降大大減少下載時間和帶寬,同時也提高的流覽器的載入速度。
也可以通過設置 no-cache 指令來禁止緩存:
Cache-Control: no-cache
更多詳情請參見w3.org。
Content-Type
這個Header包含了文檔的 mime-type 。流覽器將會依據該參數決定如何對文檔進行解析。例如,一個html頁面(或者有html輸出的php頁面)將會返回這樣的東西:
Content-Type: text/html; charset=UTF-8
text 是文檔類型,html 則是文檔子類型。 這個Header還包括了更多資訊,例如 charset 。
如果是一個圖片,將會發送這樣的回應:
Content-Type: image/gif
流覽器可以通過 mime-type 來決定使用外部程式還是自身擴展來打開該文檔。如下的例子降調用Adobe Reader:
Content-Type: application/pdf
直接載入,Apache通常會自動判斷文檔的mime-type並且添加合適的資訊到Header去。並且大部分流覽器都有一定程度的容錯,在Header未提供或者錯誤提供該資訊的情況下它會去自動檢測mime-type。
你可以在這裏找到一個常用mime-type列表。
在PHP中你可以通過 finfo_file() 來檢測檔的ime-type。
Content-Disposition
這個Header資訊將告訴流覽器打開一個檔下載視窗,而不是試圖解析該回應的內容。例如:
Content-Disposition: attachment; filename="download.zip"
他會導致流覽器出現這樣的對話方塊:

注意,適合它的 Content-Type 頭資訊同時也會被發送
Content-Type: application/zip Content-Disposition: attachment; filename="download.zip"
Content-Length
當內容將要被傳輸到流覽器時,伺服器可以通過該Header告知流覽器將要傳送檔的大小(bytes)。
Content-Length: 89123
對於檔下載來說這個資訊相當的有用。這就是為什麼流覽器知道下載進度的原因。
例如,這裏我寫了一段虛擬腳本,來模擬一個慢速下載。
// it's a zip file
header('Content-Type: application/zip');
// 1 million bytes (about 1megabyte)
header('Content-Length: 1000000');
// load a download dialogue, and save it as download.zip
header('Content-Disposition: attachment; filename="download.zip"');
// 1000 times 1000 bytes of data
for ($i = 0; $i < 1000; $i++) {
echo str_repeat(".",1000);
// sleep to slow down the download
usleep(50000);
}
結果將會是這樣的:

現在,我將Content-LengthHeader注釋掉:
// it's a zip file
header('Content-Type: application/zip');
// the browser won't know the size
// header('Content-Length: 1000000');
// load a download dialogue, and save it as download.zip
header('Content-Disposition: attachment; filename="download.zip"');
// 1000 times 1000 bytes of data
for ($i = 0; $i < 1000; $i++) {
echo str_repeat(".",1000);
// sleep to slow down the download
usleep(50000);
}
結果就變成了這樣:

這個流覽器只會告訴你已下載了多少,但不會告訴你總共需要下載多少。而且進度條也不會顯示進度。
Etag
這是另一個為緩存而產生的Header資訊。它看起來會是這樣:
Etag: "pub1259380237;gz"
伺服器可能會將該資訊和每個被發送檔一起回應給流覽器。該值可以包含文檔的最後修改日期,檔大小或者檔校驗和。流覽會把它和所接收到的文檔一起緩存。下一次當流覽器再次請求同一檔時將會發送如下的HTTP請求:
If-None-Match: "pub1259380237;gz"
如果所請求的文檔Etag值和它一致,伺服器將會發送304狀態碼,而不是200。並且不返回內容。流覽器此時就會從緩存載入該檔。
Last-Modified
顧名思義,這個Header資訊用GMT格式表明了文檔的最後修改時間:
Last-Modified: Sat, 28 Nov 2009 03:50:37 GMT
$modify_time = filemtime($file);
header("Last-Modified: " . gmdate("D, d M Y H:i:s", $modify_time) . " GMT");
它提供了另一種緩存機制。流覽器可能會發送這樣的請求:
If-Modified-Since: Sat, 28 Nov 2009 06:38:19 GMT
在If-Modified-Since一節我們已經討論過了。
Location
這個Header是用來重定向的。如果回應代碼為 301 或者 302 ,伺服器就必須發送該Header。例如,當你訪問 http://www.nettuts.com 時流覽器就會收到如下的回應:
HTTP/1.x 301 Moved Permanently
…
Location: http://net.tutsplus.com/
…
在PHP中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對訪客重定向:
header('Location: http://net.tutsplus.com/');
默認會發送302狀態碼,如果你想發送301,就這樣寫:
header('Location: http://net.tutsplus.com/', true, 301);
Set-Cookie
當一個網站需要設置或者更新你流覽的cookie資訊時,它就會使用這樣的Header:
Set-Cookie: skin=noskin; path=/; domain=.amazon.com; expires=Sun, 29-Nov-2009 21:42:28 GMT Set-Cookie: session-id=120-7333518-8165026; path=/; domain=.amazon.com; expires=Sat Feb 27 08:00:00 2010 GMT
每個cookie會作為單獨的一條Header資訊。注意,通過js設置cookie將不會出現在HTTP頭中。
在PHP中,你可以通過 setcookie() 函數來設置cookie,PHP會發送合適的HTTP 頭。
setcookie("TestCookie", "foobar");
它會發送這樣的頭資訊:
Set-Cookie: TestCookie=foobar
如果未指定到期時間,cookie就會在流覽器關閉後被刪除。
WWW-Authenticate
一個網站可能會通過HTTP發送這個Header資訊來驗證用戶。當流覽器看到Header有這個回應時就會打開一個彈出窗。
WWW-Authenticate: Basic realm="Restricted Area"
它會看起來像這樣:

在PHP手冊的一章中就有一段簡單的代碼演示了如果用PHP做這樣的事情:
if (!isset($_SERVER['PHP_AUTH_USER'])) {
header('WWW-Authenticate: Basic realm="My Realm"');
header('HTTP/1.0 401 Unauthorized');
echo 'Text to send if user hits Cancel button';
exit;
}
else {
echo
"Hello {$_SERVER['PHP_AUTH_USER']}.";
echo
"You entered {$_SERVER['PHP_AUTH_PW']} as your password.";
}
Content-Encoding
這個Header通常會在返回內容被壓縮時設置。